 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近日,單位組織迎“五一”讀書(shū)活動(dòng),讓職工們做閱讀分享。作為一名在礦山工作的女職工,我和大家分享的是講述上世紀(jì)70年代煤礦女職工的工作、愛(ài)情和生活的一部小說(shuō)《女工繪》(劉慶邦著,作家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)。
打開(kāi)《女工繪》,撲面而來(lái)的是熟悉的場(chǎng)景:“拉煤的火車(chē)響著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汽笛聲,在井下忙碌了一班的礦工,臉是黑的,鼻子是黑的,眼瞼是黑的,像戴了一張用黑膠皮做成的面具……”這些礦山里的尋常風(fēng)景,于我是親切、溫暖的。
書(shū)的前半部,我讀起來(lái)輕松、愉快。從東風(fēng)礦的宣傳隊(duì)成立開(kāi)始,小說(shuō)情節(jié)發(fā)生了轉(zhuǎn)向,讓人越讀心中越不是滋味兒。
那個(gè)年代,礦山的管理理念、規(guī)章制度都比較落后,職工的家庭成分、作風(fēng)問(wèn)題被看得很重,許多職工尤其是女職工,工作生活的環(huán)境很不友好。一直謹(jǐn)言慎行、隱忍求全、刻苦訓(xùn)練、不怕吃苦的陳秀明、楊海平等女職工,本以為被選入宣傳隊(duì),就能撕掉貼在身上的成分、作風(fēng)標(biāo)簽,可這小小的心愿在當(dāng)時(shí)很難實(shí)現(xiàn)。
宣傳隊(duì)成立沒(méi)多久就解散了,她們又回了原來(lái)的崗位。陳秀明重回食堂,繼續(xù)隱忍著“孫班長(zhǎng)”之流的打壓和嘲諷;楊海平又回到了理發(fā)店,不得不再次面對(duì)一些礦工明里玩笑、暗里調(diào)戲的葷言葷語(yǔ)……
在這群女工中,最懂得生活智慧的莫過(guò)于華春堂了。在礦山,她知道什么時(shí)候該說(shuō)話、什么時(shí)候僅僅依靠沉默就能換來(lái)想要的工作,宣傳隊(duì)解散后,也只有她如愿進(jìn)了礦區(qū)最好的技術(shù)部門(mén)--化驗(yàn)室。在終身大事上,華春堂深諳“幸福要靠自己抓住”的道理,快速鎖定目標(biāo)、主動(dòng)出擊,很快與心儀的對(duì)象確定了戀愛(ài)關(guān)系。
本以為華春堂的故事能讓人松一口氣,可作者筆鋒一轉(zhuǎn),讓她在結(jié)婚的前夕死于一場(chǎng)車(chē)禍。為什么這樣寫(xiě)?仔細(xì)思考,或許這便是作者對(duì)個(gè)體命運(yùn)與時(shí)代大環(huán)境之間復(fù)雜關(guān)系的深刻認(rèn)識(shí)。假如華春堂沒(méi)有經(jīng)歷那場(chǎng)意外,而是如愿結(jié)婚、生子,此后的生活就一定會(huì)幸福嗎?這恐怕還要打上個(gè)問(wèn)號(hào),華春堂的悲劇固然有時(shí)代的因素,可她自己也是個(gè)矛盾體--她“有眼光”,卻把這眼光盯在了“換工作”“找對(duì)象”等外在因素上,她從未深入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、本領(lǐng),這種外在的所求注定不會(huì)長(zhǎng)久。
書(shū)中有一個(gè)小細(xì)節(jié),讓我感觸頗深。華春堂走在礦區(qū)的路上,她意識(shí)到,地上有一個(gè)世界,地下還有一個(gè)世界。這是空間的區(qū)分,那時(shí)候,井上的工作安全、待遇好,多數(shù)工人都向往井上的工作。
同樣身為礦山女工的我,與華春堂也身處兩個(gè)世界:書(shū)中半個(gè)世紀(jì)前的那個(gè)煤礦和書(shū)外現(xiàn)在的煤礦。而今,我所在的礦山管理先進(jìn)、制度規(guī)范,大家齊心協(xié)力抓生產(chǎn)、謀發(fā)展。我們有宣傳隊(duì)、籃球隊(duì)、詩(shī)詞協(xié)會(huì)、書(shū)法協(xié)會(huì)等組織,平日里經(jīng)常舉辦文藝匯演、廣場(chǎng)舞大賽、歌唱比賽等,職工們的工作生活環(huán)境舒心、雅致。
《女工繪》的讀書(shū)分享喚起了不少老職工的青春回憶,他們紛紛表示,短短幾十年,礦山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華春堂、陳秀明、楊海平等人的經(jīng)歷讓大家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,我們會(huì)以全新的面貌,展示新時(shí)代礦山女工的風(fēng)采。
關(guān)鍵詞: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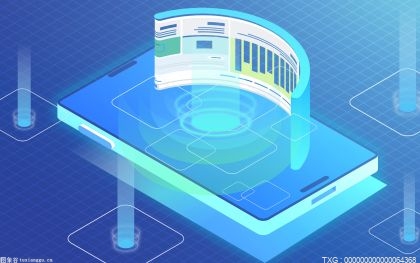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 營(yíng)業(yè)執(zhí)照公示信息
營(yíng)業(yè)執(zhí)照公示信息